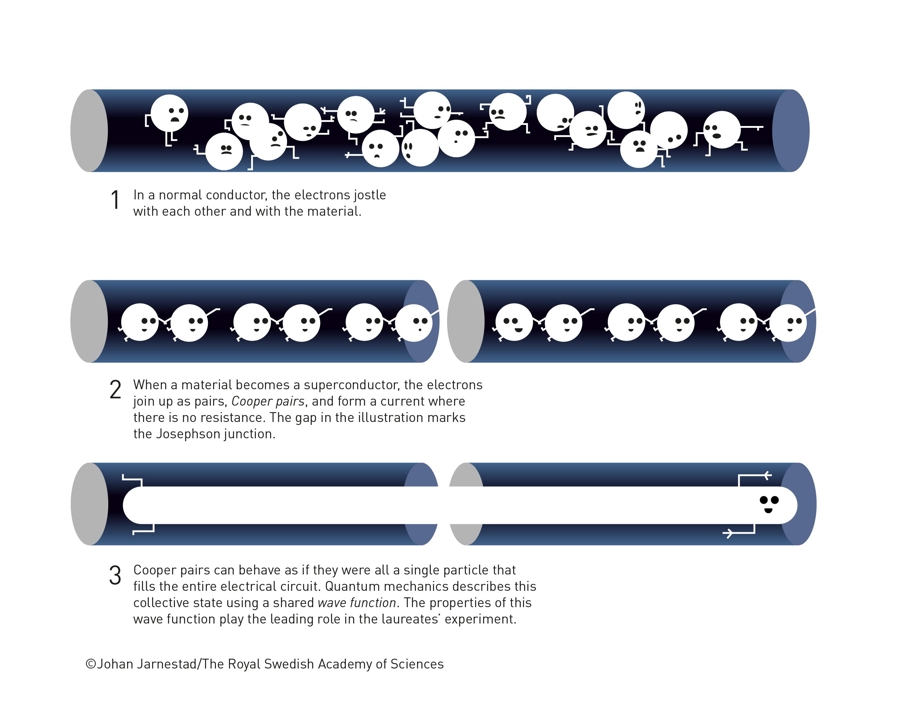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0月7日颁出,三位美国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耶鲁大学的米歇尔·H·德沃雷特(Michel H. Devoret)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约翰·M·马蒂尼斯(John M. Martinis),因为“在电路中发现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共同获得今年的诺奖。
今年是海森堡创立矩阵力学(量子力学三种表达形式之一)100周年,所以今年也被联合国定为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在此次颁奖前,学界就普遍预测,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可能会授予量子领域。
当然,在科学界看来,此次诺奖表彰的不仅是三位科学家发现了一项深奥难懂的量子物理现象,更是因为他们的发现推开了量子计算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的大门。他们的研究,堪称是发现了一个全新产业生态的“点火装置”,并参与推动这个产业生态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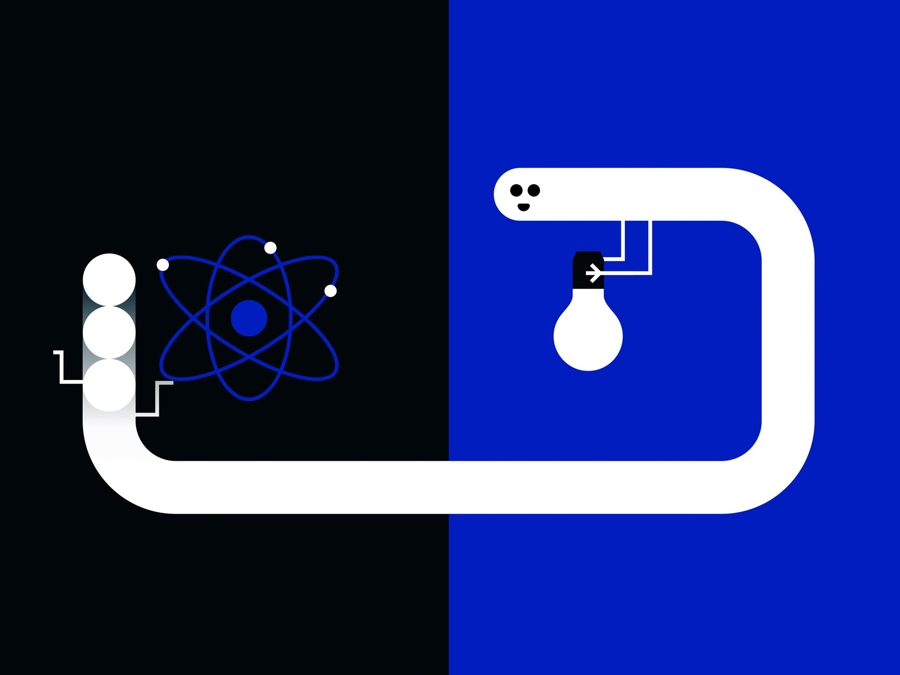
一个改变世界的实验
按照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奖词,三位科学家使用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量子世界的奇异特性不仅仅存在于原子态,在大到毫米的器件中也同样存在。简言之,他们因为宏观量子效应的发现而获奖。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李晓鹏介绍,经典的电学描述的往往是电流跟电压、电容、电感、电阻之间的简单关系,大多数人在中学就学过相关知识。而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单个粒子尺度上的特性,这些在量子力学领域被称为微观现象。比如,量子的隧穿效应,简单说,就是单个粒子有时会在其微观世界中直接穿过障碍物的现象,而不是像宏观世界中一个物体遇到障碍物往往会反弹回来。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际上是表彰了展示如何在宏观尺度上观察量子隧穿的实验。
1984年和1985年,克拉克和他当时指导的博士后德沃雷特、博士研究生马蒂尼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用两个超导体,即可以无电阻导电的元件,构建了一个电路。在这个实验中,该系统通过隧穿逃离零电压状态、产生电压,从而显示出其量子特性。三位科学家的研究还表明,该系统是量子化的,这意味着它只以特定数量吸收或发射能量。
解读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湖南师范大学超导量子器件专家彭智慧教授指出,克拉克的研究是量子比特出现的先驱性研究。宏观量子效应的实验验证(如人工原子的量子特性验证),为后续超导量子比特和超导量子计算铺路。也正因此,此次颁奖被解读为诺贝尔委员会对利用超导量子器件进行量子力学基本原理验证的认可。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黄吉平表示,这三位科学家的工作可说是将“幽灵般”的量子行为从原子世界拓展至我们肉眼可见的尺度。他们借助特殊的超导电路,如同搭建“量子乐高”一般,首次让一个宏观电路精准且清晰地呈现出“能量台阶”(即“能量量子化”)现象和“隔空穿越”效应。
这一成果不仅对物理学基础产生了巨大震撼,更直接推动了如今我们正全力构建的量子计算机的发展。它有力地证明,量子世界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存在于我们精心设计的电路之中。这里的“电路”绝非普通的家用电路,而是一种经过特殊设计和制造的微观或介观电路,核心是 “超导电路”。其中,主要有两类关键电路元件,即LC振荡回路和约瑟夫森结。
彭智慧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该研究成果还可应用于量子传感领域。例如,利用其对微波信号的超高灵敏度,可探测单个能量极低、传统手段难以捕捉的微波光子。其他的潜在应用还包括量子增强雷达、轴子、暗光子等暗物质候选粒子探测等前沿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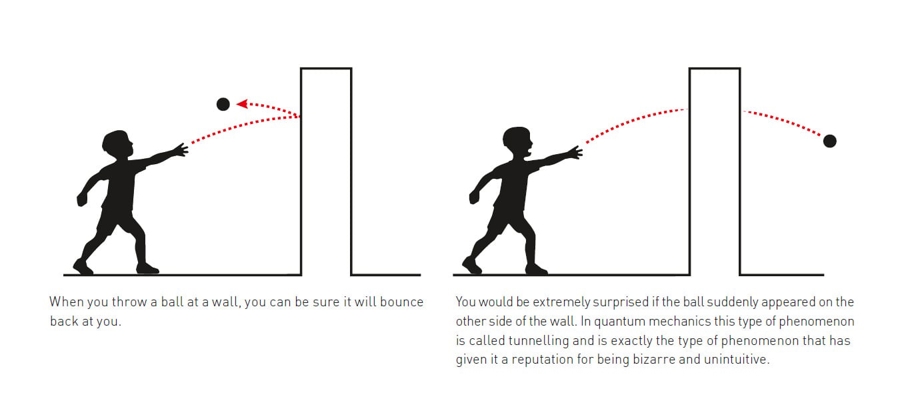
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今年的诺奖有点特别,奖励的不只是这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发现,更是间接地对他们成果的工程化以及应用落地的奖励。”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凝聚态物理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应江华认为,尤其是马蒂尼斯的得奖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他可说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工程化和应用落地的旗帜性人物。”
而新晋诺奖得主德沃雷特就拥有一家超导量子计算的创业公司,另一位获奖者马蒂尼斯则曾经是谷歌超导计算团队的负责人,他也被认为是超导量子计算的领军人物。马蒂尼斯最重要的贡献是证明了量子计算的优越性,这是他在谷歌时完成的工作,被认为是“量子计算的开端”。在应江华看来,“今年这个诺奖,将会对超导量子计算领域带来巨大的推动。”三位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了“宏观电路能够作为操控量子效应的稳定载体”,进而为工程技术人员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使他们能运用标准的微电子制造技术来设计并构建量子设备。
李晓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进一步谈到,量子计算可说是全球技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当前,多个国家都在发展量子计算产业。李晓鹏也坦言,“中国的量子计算与美国的发展算是旗鼓相当,但是在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积累等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
据悉,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相关研究的单位。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教授领导、朱晓波教授负责的团队与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等团队同处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朱晓波领导的团队,在超导量子计算实验研究方面与谷歌团队竞争激烈。